
週日頂著豔陽,去淡水看爸爸。
昨晚打電話給他,手機沒開、家裡電話沒人接,我以為沒人,就算了。
15 分鐘後,他打電話來,劈頭就是帶著憤怒的吼叫: 「你都不管我了死活啦?!」
「你都不來看我啊?」
*
到家的時候,他在睡覺,歪著頭,下半身沒有穿褲子,包著紙尿褲。我輕推他的手,他的臉頰凹陷(因為沒有戴假牙),我深怕,他感受不到我在叫他…… 他又開始唸我不結婚,老了沒人照顧。
「這世上這麼多人沒有婚姻,也沒聽見他們都很慘啊?重點不是婚姻。」
「那重點是什麼?」
「重點是你想不想過好自己的生活,並且不要一直干涉別人的生活。」
其實我還蠻想跟他說只要同志婚姻合法化,我一樣可以結婚的,不過短時間內還是算了,他開始念哥哥。
「你幹嘛跟他講這麼多?他已經長這麼大了,他要對他自己的人生負責啊。」
「但是,我還是要提醒他啊!」
「提醒了,有用嗎?如果有用,早就有用了。」
「…..那是因為我之前沒有提醒啊!」
「你已經提醒過很多年了。你管好你自己就好。」
我們的對話的確是父子對話,但他更像兒子。
我回家一小時,他和生我那女人爭執了四次,我一句:「好了,不要吵了,這沒有什麼好吵的。」共說了三次,他們無法理性溝通超過三句話,像是年邁的毛毛對著印尼看護不停低聲怒吼,都是一種反射性動作。
家裡大致上有打掃過,有了印傭至少有人打掃,可我走進浴室洗手,一隻大大的蟑螂棲身在洗手臺上跟我打招呼,兩支細長的觸角不停晃動。
無論是客廳,或是毛毛休息的房間角落,都有著一股氣味 --- 腐敗的氣味;混著汗酸味,毛毛的身上也是那種氣味,毛毛兩隻眼睛都看不見了,牠走路全憑直覺,牠想對看護吠叫,卻總是跑進空無一人的房間,偶爾撞牆,牠今天精神不錯,我進門時,從房間裡走出來磨蹭一下,又轉身躲進房間。
牠還記得我嗎?
無論是爸爸、生我那女人還是毛毛,我都已經不再是他們生活裡的一部分了,我像是一個過客,久久來一次,他們的氣味令我生厭,一離開那棟房子,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濕紙巾擦拭手、臉,還用綠油精塗抹鼻子與人中,生怕帶回家一絲不愉快的空氣。
今晚 K 打電話來的機會不高。 他這週因為教召,從花蓮去淡水,我們說好如果沒有重要的事情,就不特別打電話。
*
我關掉冷氣,打開書房的窗戶。
窗外的聲音頓時湧進來,有狗叫、有車聲;還有男人交談的聲音…..週日晚間十點,七月底,小孩子正在放暑假,樓下國泰與鄰居開心地在店門口烤肉,我打開剛剛下載的 Bjork 的特別節目,昨天,她正在日本 Fuji Rock festival 演出,只要再等不到三週,我就能在台北看到她。
親愛的你:
我們那樣地不同。
我把上週五晚上去看大爺爺的外孫羅倫的故事寫在公開的臉書帳號,有一位同事說我的文字讓她想到張大春「聆聽父親」那本書,但我的故事比較風趣幽默。本來想要回覆:「我沒有很喜歡張大春,我比較希望我的文字像張愛玲;畢竟張愛玲總比張大春來得有深度……」可我什麼都沒說。
Bjork 在節目裡與一個老人對談,不時穿插著禽鳥的鳴叫,還有雨林中的猿猴….各式各樣的聲音,她喜歡這些原始之聲。
K 一直想去亞馬遜雨林探險。
我們那樣地不同。
爸爸曾經在我國三時,在聯絡簿上寫:「我一點都不了解他,如果可能的話,請老師告訴我他在想什麼。」 但老師也不懂我在想什麼。
我曾經跟老師說: 「我不是一個會主動告訴別人『我現在在想什麼』的人 --- 除非你在對的時間點或是對的機緣;用對的方式問我,我很直接,我想要回答的時候,我不會保留,可你得問我。」
對於別人的問題,我不一定會回答,但只要回答,我就一定說我想說的,不會掩飾,不會拐彎抹角;我從來不會考慮別人接受度的問題,但我亦沒有
*
離開淡水的時候,我在聽雷光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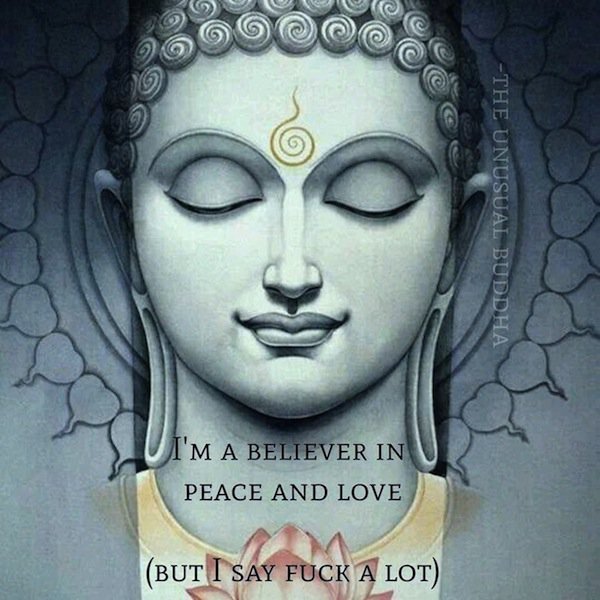
發表留言